жң¬ж–Үз”ұ жё еҺҝзҪ‘ www.quxian.cn ж•ҙзҗҶжҸҗдҫӣпјҡ
еҢ—еӨ§ж•ҷжҺҲпјҡзҺ°еңЁж•ҷеёҲж•ҙдҪ“ж°ҙеҮҶд№ҹи®ёдёҚдҪҺдәҺж°‘еӣҪж—¶

еҢ—дә¬еӨ§еӯҰе“ІеӯҰзі»ж•ҷжҺҲдҪ•жҖҖе®ҸгҖӮ
еҢ—дә¬еӨ§еӯҰе“ІеӯҰзі»ж•ҷжҺҲдҪ•жҖҖе®Ҹиҝ‘ж—ҘжқҘеҲ°еӨҚж—ҰеӨ§еӯҰпјҢдҪңдёәеӨҚж—ҰеӨ§еӯҰе“ІеӯҰеӯҰйҷў60е‘Ёе№ҙйҷўпјҲзі»пјүеәҶзі»еҲ—жј”и®Ізҡ„дё»и®ІдәәпјҢдёҺдј—дәәеҲҶдә«гҖҠз”ҹе‘Ҫзҡ„д»Һе®№дёҺжү§зқҖдёҖдёҖзҪ—е°”ж–Ҝзҡ„е“ІеӯҰжҺўзҙўгҖӢзҡ„иҜқйўҳгҖӮ
зҪ—е°”ж–ҜжҳҜзҫҺеӣҪд№ғиҮіиҘҝж–№20дё–зәӘжңҖйҮҚиҰҒзҡ„йҒ“еҫ·е’Ңж”ҝжІ»е“ІеӯҰ家д№ӢдёҖпјҢе…¶дё»иҰҒзҡ„жҖқжғіиҙЎзҢ®жҳҜжңүе…ізӨҫдјҡжӯЈд№үгҖҒж”ҝжІ»иҮӘз”ұдё»д№үд»ҘеҸҠеӣҪйҷ…жі•зҡ„е“ІеӯҰзҗҶи®әгҖӮдҪ•жҖҖе®Ҹж•ҷжҺҲжҳҜзҪ—е°”ж–ҜгҖҠжӯЈд№үи®әгҖӢзҡ„дё»иҜ‘гҖӮ
2016е№ҙ10жңҲ29ж—ҘпјҢеӨҚж—ҰеӨ§еӯҰе“ІеӯҰеӯҰйҷўе°ҶиҝҺжқҘе»әзі»60е‘Ёе№ҙгҖҒе»әйҷў10е‘Ёе№ҙзҡ„еәҶе…ёж—ҘгҖӮдёҖз”Іеӯҗзҡ„иҪ®еӣһпјҢ вҖңжүҺж №еӯҰжңҜпјҢе®ҲжҠӨжҖқжғіпјҢеј•йўҶзӨҫдјҡвҖқе§Ӣз»ҲжҳҜеӨҚж—ҰеӨ§еӯҰе“ІеӯҰеӯҰ科зҡ„дј з»ҹпјҢвҖңе“ІеӯҰзҡ„ж—¶д»ЈжӢ…еҪ“вҖқжҳҜ60е‘Ёе№ҙйҷўпјҲзі»пјүеәҶзҡ„дё»йўҳгҖӮ
дҪ•жҖҖе®ҸпјҢиҝҷдҪҚиў«еӯЈзҫЎжһ—е…Ҳз”ҹз§°иөһвҖңзІҫеҪ©вҖқзҡ„е“ІеӯҰж•ҷжҺҲпјҢж“…й•ҝйҖҡиҝҮеҸҷиҝ°зҡ„ж–№ејҸе°Ҷз”ҹе‘Ҫзҡ„е“ІзҗҶеЁ“еЁ“йҒ“жқҘгҖӮеңЁжӯӨж¬Ўи®ҝй—®еӨҚж—Ұе“ІеӯҰеӯҰйҷўжңҹй—ҙпјҢдҪ•жҖҖе®Ҹж•ҷжҺҲжҺҘеҸ—дәҶжҫҺж№ғж–°й—»зҡ„дё“и®ҝпјҢи°ҲеҸҠд»–жүҖзҗҶи§Јзҡ„е…¬е№ідёҺжӯЈд№үпјҢйҒ“еҫ·дёҺ规еҲҷд»ҘеҸҠе…¬ж°‘ж•ҷиӮІгҖҒз”ҹе‘Ҫж•ҷиӮІзӯүиҜқйўҳгҖӮ
гҖҗеҜ№иҜқдҪ•жҖҖе®ҸгҖ‘
и°Ҳе…¬ж°‘ж•ҷиӮІпјҡдёҚйңҖиҰҒжҠҠйҒ“еҫ·й«ҳе°ҡеҢ–пјҢйҒ“еҫ·еҚіи§„еҲҷ
жҫҺж№ғж–°й—»пјҡжӮЁзҡ„дё“и‘—е’ҢиҜ‘и‘—зӣёеҪ“еӨҡпјҢе…¶дёӯдёҠдёӘдё–зәӘ90е№ҙд»Јзҡ„гҖҠиүҜеҝғи®әв”Җв”Җдј з»ҹиүҜзҹҘзҡ„зӨҫдјҡиҪ¬еҢ–гҖӢпјҢдёҖзӣҙеҲ°д»ҠеӨ©йғҪеңЁеҪұе“ҚзқҖзӨҫдјҡгҖӮи·қзҰ»жӮЁеҶҷиҝҷжң¬д№Ұе·Із»Ҹ20еӨҡе№ҙиҝҮеҺ»дәҶпјҢжӮЁи§үеҫ—дёӯеӣҪз»ҸиҝҮиҝҷд№ҲеӨҡе№ҙзҡ„еҸ‘еұ•пјҢзӨҫдјҡиҪ¬еһӢжңҹдәә们жүҖйқўдёҙзҡ„з§Қз§ҚйҒ“еҫ·еӣ°жғ‘пјҢиҝҷжң¬д№ҰдёӯжүҖдј йҖ’еҮәзҡ„жҖқжғіиҝҳжңүе“ӘдәӣзҺ°е®һзҡ„еҗҜзӨәж„Ҹд№үпјҹ
дҪ•жҖҖе®ҸпјҡжҲ‘зҡ„гҖҠиүҜеҝғи®әгҖӢжҳҜ20еӨҡе№ҙеүҚеҶҷзҡ„пјҢзҺ°д»ЈзӨҫдјҡиө°еҗ‘е№ізӯүжҳҜеӨ§еҠҝжүҖи¶ӢпјҢжүҖд»ҘеҗӣеӯҗдјҰзҗҶгҖҒзІҫиӢұдјҰзҗҶдёҚеҶҚжҳҜдё»жөҒпјҢдёҚеҶҚжҳҜи®©е°‘ж•°ж–ҮеҢ–дјҳи¶Ҡзҡ„дәәжқҘеј•еҜјзӨҫдјҡгҖӮзҺ°еңЁжҲ‘们еҝ…йЎ»иҰҒжіЁж„ҸеҲ°зӨҫдјҡе·Із»ҸеңЁж”№еҸҳзҡ„зҺ°е®һпјҢзҪ‘дёҠиҝ‘жңҹзғӯдј иҝҮиғЎйҖӮи°ҲйҒ“еҫ·дёҺ规еҲҷзҡ„дёҖж®өиҜқпјҢз§°иғЎйҖӮиҜҙпјҡвҖңдёҖдёӘиӮ®и„Ҹзҡ„еӣҪ家пјҢеҰӮжһңдәәдәә讲规еҲҷиҖҢдёҚжҳҜи°ҲйҒ“еҫ·пјҢжңҖз»ҲдјҡеҸҳжҲҗдёҖдёӘжңүдәәе‘іе„ҝзҡ„жӯЈеёёеӣҪ家пјҢйҒ“еҫ·иҮӘ然дјҡйҖҗжёҗеӣһеҪ’пјӣдёҖдёӘе№ІеҮҖзҡ„еӣҪ家пјҢеҰӮжһңдәәдәәйғҪдёҚ讲规еҲҷеҚҙеӨ§и°ҲйҒ“еҫ·пјҢи°Ҳй«ҳе°ҡпјҢеӨ©еӨ©жІЎдәӢе„ҝе°ұи°ҲйҒ“еҫ·и§„иҢғпјҢдәәдәәеӨ§е…¬ж— з§ҒпјҢжңҖз»ҲиҝҷдёӘеӣҪ家дјҡе •иҗҪжҲҗдёәдёҖдёӘдјӘеҗӣеӯҗйҒҚеёғзҡ„иӮ®и„ҸеӣҪ家гҖӮвҖқ
жҲ‘жӣҫз»ҸеӨҡж–№жұӮиҜҒиҝҮпјҢиҝҷдәӣиҜқеҫҲеҸҜиғҪ并дёҚжҳҜиғЎйҖӮе…Ҳз”ҹзҡ„еҺҹиҜқпјҢдҪҶиғҢеҗҺеҸҚжҳ дәҶзҺ°д»ЈзӨҫдјҡдёҖз§ҚжөҒиЎҢзҡ„ж„ҸиҜҶпјҡеҚіи§„еҲҷжҜ”йҒ“еҫ·жӣҙдјҳе…ҲпјҢиҝҷжҳҜжңүйҒ“зҗҶзҡ„гҖӮж—¶дёӢи°ҲвҖңйҒ“еҫ·вҖқеҚҙеёёеёёеӨҡжңүеҗ«ж··пјҢеҸ—дј з»ҹзҡ„вҖңйҒ“еҫ·вҖқжҰӮеҝөеҪұе“ҚиҫғеӨ§гҖӮдј з»ҹзҡ„гҖҒд№ғиҮіиҪ¬еһӢж—¶жңҹзҡ„дәә们жүҖиҜҙзҡ„вҖңйҒ“еҫ·вҖқжҰӮеҝөеҫҖеҫҖжҳҜжҢҮй«ҳе°ҡзҡ„йҒ“еҫ·пјҢеҚіеёҢеңЈеёҢиҙӨгҖҒиӢұйӣ„жҘ·жЁЎзҡ„дјҰзҗҶпјҢиҖҢдёҠйқўдёҖж®өжүҖиҜҙзҡ„вҖң规еҲҷвҖқе…¶е®һе°ұжҳҜзҺ°д»Јзҡ„дјҰзҗҶпјҢ并дёҚдёҺвҖңйҒ“еҫ·вҖқзҡ„зҺ°д»Јеҗ«д№үеҶІзӘҒпјҢжҲ–иҖ…иҜҙвҖң规еҲҷвҖқзҡ„еҹәжң¬еҶ…е®№е…¶е®һе°ұжҳҜдјҰзҗҶгҖӮзҺ°д»ЈдјҰзҗҶдёҚжҳҜд»Ҙдәәзҡ„дҝ®иә«е…»жҖ§пјҢиҮ»дәҺиҮіе–„дёәдёӯеҝғпјҢиҖҢжҳҜд»ҘеұҘиЎҢеҹәжң¬и§„еҲҷгҖҒ规иҢғдёәдёӯеҝғпјҢе’Ңжі•еҫӢ规иҢғгҖҒеҒҡдәә规еҲҷеӨҡжңүйҮҚеҗҲпјҢйҰ–иҰҒзҡ„иЎҢдёә规еҲҷжҳҜдёҚиғҪжқҖжҲ®е’ҢдјӨе®іж— иҫңиҖ…гҖӮжҲ‘д»ҘеүҚжүҖеҶҷзҡ„гҖҠиүҜеҝғи®әгҖӢд№ҹжҳҜжғіиҰҒи§ЈеҶіиҝҷдёӘеҹәжң¬и§„еҲҷзҡ„дјҰзҗҶй—®йўҳпјҢеӨ„зҗҶиҝҷдёӘеҹәжң¬д№үеҠЎзҡ„дјҰзҗҶй—®йўҳгҖӮ
жҫҺж№ғж–°й—»пјҡиҫҪе®Ғдәәж°‘еҮәзүҲзӨҫ1998е№ҙеҮәзүҲдәҶжӮЁзҡ„дё“и‘—гҖҠеә•зәҝдјҰзҗҶгҖӢпјҢзҺ°еңЁеҢ»жӮЈе…ізі»зҹӣзӣҫзӘҒеҮәпјҢж”ҝеәңе’Ңж°‘дј—д№Ӣй—ҙзҡ„е…ізі»д№ҹ并дёҚзј“е’ҢпјҢжҜ”еҰӮйӣ·жҙӢжЎҲгҖҒжҜ”еҰӮйӯҸеҲҷиҘҝдәӢ件пјҢж”ҝеәңгҖҒзӨҫдјҡгҖҒдёӘдәәзӯүж–№ж–№йқўйқўеә”иҜҘйҒөе®ҲжҖҺж ·зҡ„еә•зәҝдјҰзҗҶпјҹ
дҪ•жҖҖе®ҸпјҡеңЁеә•зәҝдјҰзҗҶйқўеүҚпјҢж”ҝеәңгҖҒзӨҫдјҡгҖҒдёӘдәәжҳҜеҗҢзӯүзҡ„гҖӮж— и®әжҳҜж”ҝеәңгҖҒзӨҫдјҡиҝҳжҳҜдёӘдәәпјҢйғҪеә”иҜҘжүҝжӢ…дёҖдәӣеҹәжң¬зҡ„дјҰзҗҶпјҢжҜ”еҰӮеҲ¶еәҰзҡ„жӯЈд№үпјҢдёӘдәәзҡ„д№үеҠЎгҖҒиҙЈд»»гҖҒеҗҢжғ…еҝғгҖҒжҒ»йҡҗд№ӢеҝғгҖҒ敬д№үгҖҒжҳҺзҗҶзӯүпјҢзӣ®еүҚзӨҫдјҡзҡ„иҪ¬еһӢиҝҳжІЎжңүе®ҢжҲҗпјҢеҶҚжқҘжҸҗиүҜеҝғи®әд»ҘеҸҠ规еҲҷе’ҢйҒ“еҫ·д»ҚжңүзҺ°е®һж„Ҹд№үгҖӮжҲ‘зҡ„гҖҠиүҜеҝғи®әгҖӢиҝҷжң¬д№ҰеҮәзүҲж—¶пјҢдҪ•е…үжІӘжӣҫз»ҸжңүдёҖдёӘиҜ„и®әпјҢз§°д№ҰдёӯжүҖжҸҗеҸҠзҡ„и§ӮзӮ№пјҢдёҚд»…иҝҮеҺ»150е№ҙйңҖиҰҒйҮҚи§ҶпјҢд»ҠеҗҺзҡ„150е№ҙд№ҹйңҖиҰҒйҮҚи§ҶгҖӮжҲ‘们зҡ„зЎ®дёҚйңҖиҰҒй«ҳи№ҲжҲ–й«ҳи°ғзҡ„дјҰзҗҶпјҢиҖҢйңҖиҰҒйҰ–е…ҲйҒөе®Ҳеҹәжң¬зҡ„иЎҢдёә规иҢғпјҢеҚіеә•зәҝдјҰзҗҶгҖӮ
е…¬ж°‘ж•ҷиӮІеҲ°дәҶзҺ°еңЁжӣҙеҠ иҝ«еҲҮпјҢиҝӣе…ҘеӯҰж ЎпјҢе°ұжҳҜиҝӣе…Ҙж•ҷиӮІеҲ¶еәҰпјҢдёҚжҳҜз®ҖеҚ•зҡ„зҹҘиҜҶеӯҰд№ пјҢиҖҢжҳҜиЎҢдёәе’Ңд№ жғҜзҡ„е…»жҲҗгҖӮжҜ”еҰӮзҫҺеӣҪе°ҸеӯҰеҒҡд»Җд№ҲдәӢиҖҒжҳҜжҺ’йҳҹпјҢеҲқзңӢиө·жқҘжҢәзғҰдәәзҡ„пјҢж—©жҷЁж—©еҲ°дәҶд№ҹдёҚиғҪе…Ҳиҝӣж•ҷе®ӨпјҢеҲ°дәҶж—¶й—ҙеҶҚжҺ’йҳҹиҝӣж•ҷе®ӨпјҢиҝҳжңүеғҸеңЁж“ҚеңәдёҠжҠ•зҗғпјҢдёӯеҚҲеҗғйҘӯпјҢйғҪжҳҜжҺ’йҳҹзҡ„пјҢдҪҶд№…иҖҢд№…д№ӢпјҢе°ұжҲҗдәҶд№ жғҜдәҶгҖӮеҚідҪҝй•ҝеӨ§еҗҺпјҢжҺ’йҳҹд№ҹжҲҗдёәдәҶдёҖз§ҚиҮӘи§үпјҢеӣ дёә他们д»Һе°Ҹе°ұжҳҜиҝҷж ·зҡ„е…»жҲҗж•ҷиӮІгҖӮ
йҒ“еҫ·жҳҜдёҖдёӘж•ҷеҢ–зҡ„иҝҮзЁӢпјҢдёҚжҳҜеӨ©з”ҹзҡ„пјҢ规еҲҷд№ҹйңҖиҰҒйҖҡиҝҮе…»жҲҗж•ҷиӮІпјҢеҫ·иЎҢзҡ„е…»жҲҗпјҢжҳҜйңҖиҰҒдёҖд»Јд»Јз§ҜзҙҜзҡ„гҖӮ зҺ°д»ЈдәәеӨӘжҖҘдәҶпјҢйқўеҜ№зӨҫдјҡзҡ„жҡҙеҠӣеҖҫеҗ‘пјҢжӣҙеә”иҜҘеҺ»йҒөиЎҢеә•зәҝзҡ„дјҰзҗҶпјҢйңҖиҰҒеңЁж•ҷиӮІзҡ„еҹәжң¬иҰҒжұӮдёӢиҝӣиЎҢйҒ“еҫ·зҡ„и®ӯз»ғпјҢиҝӣиЎҢдәәж јзҡ„е…»жҲҗе’Ңеҹ№е…»пјҢжүҚиғҪеҪўжҲҗжӣҙеҠ жҲҗзҶҹгҖҒзҗҶжҖ§зҡ„зӨҫдјҡгҖӮйҒөе®Ҳ规еҲҷе…¶е®һе°ұжҳҜйҒөе®ҲйҒ“еҫ·пјҢиҝҷж„Ҹе‘ізқҖеҜ№д»–дәәзҡ„е°ҠйҮҚпјҢжҠҠеҲ«дәәзңӢжҲҗе№ізӯүзҡ„дёӘдҪ“пјҢеҗҰе®ҡдёҖеҲҮйҒ“еҫ·пјҢе°ұжҳҜйҒ“еҫ·иҷҡж— дё»д№үгҖӮдҪҶй«ҳи°ғзҡ„йҒ“еҫ·д№ҹжҳҜдёҖдёӘжһҒз«ҜпјҢд№ҹеҫҲйҡҫејәеҲ¶жҖ§ең°иҰҒжұӮжүҖжңүдәәеҒҡеҲ°пјҢиҖҢеә”иҜҘи®©жҸҗеҖЎиҖ…зҺҮе…ҲзӨәиҢғпјҢиҮӘи§үиҝҪжұӮгҖӮзҺ°д»ЈйҒ“еҫ·е°ұжҳҜе®Ҳ规еҲҷпјҢеҒҡеҲ°иҝҷдәӣпјҢе°ұдёҚеӨұдёәдёҖдёӘжӯЈзӣҙзҡ„дәәгҖҒжӯЈжҙҫзҡ„дәәгҖӮ
иҝҮеҺ»зҡ„дјҰзҗҶеҜ№з»ҹжІ»иҖ…е’ҢжқғеҠӣиҖ…иҰҒжұӮжӣҙй«ҳпјҢжқғиҙЈжҳҜе‘ҲжӯЈжҜ”зҡ„е…ізі»пјҢжқғеҠӣи¶ҠеӨ§пјҢе°ұеә”иҜҘжүҝжӢ…жӣҙеӨ§зҡ„иҙЈд»»гҖӮ
д»ҘзҷҫеәҰдёәдҫӢпјҢе®ғжҳҜдёӯеӣҪжңҖеӨ§зҡ„жҗңзҙўеј•ж“ҺпјҢжүҖд»ҘеңЁдҝЎд»»еәҰдёҠиҰҒжүҝжӢ…жӣҙеӨ§зҡ„иҙЈд»»гҖӮжүҖд»ҘйӯҸеҲҷиҘҝдәӢ件引еҸ‘дәҶиҪ©з„¶еӨ§жіўпјҢеӨ§еӯҰз”ҹжӮЈдәҶзҪ•и§Ғз—…пјҢжұӮз”ҹж¬ІжңӣејәзғҲпјҢйҖҡиҝҮзҪ‘з»ңжҹҘиҜўпјҢз»“жһңиў«зҪ‘з»ңдёҠзҡ„з«һд»·жҺ’еҗҚе№ҝе‘ҠжүҖиҜҜеҜјгҖӮеҶҚжҜ”еҰӮеҢ»жӮЈзҹӣзӣҫзӘҒеҮәпјҢе…ЁеӣҪеҗ„ең°дјӨеҢ»дәӢ件频еҸ‘гҖӮйңҖиҰҒжқғиҙЈеҲҶжҳҺпјҢиҖҢдё”дёҚе…Ғи®ёжңүзү№жқғзҡ„еӯҳеңЁпјҢжүҝжӢ…иҙЈд»»зҡ„е…·дҪ“жғ…еҶөйңҖиҝӣиЎҢе…·дҪ“еҲҶжһҗгҖӮ
и°Ҳж•ҷиӮІе…¬е№іпјҡж•ҷиӮІеӨҡиҪЁеҲ¶жүҚиғҪи®©ж•ҷиӮІж”№йқ©иҝӣжӯҘ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еҖ’йҖҖ
жҫҺж№ғж–°й—»пјҡдёӯеӣҪзӨҫдјҡ科еӯҰеҮәзүҲзӨҫ1991е№ҙеҮәзүҲдәҶжӮЁзҡ„иҜ‘и‘—гҖҠж— ж”ҝеәңгҖҒеӣҪ家дёҺд№ҢжүҳйӮҰгҖӢпјҢеңЁжӮЁзҡ„и®әж–ҮдёӯпјҢд№ҹжҸҗеҸҠиҝҮеӨҡж¬Ўд№ҢжүҳйӮҰгҖӮзӣ®еүҚжӯЈжҳҜй«ҳиҖғжӢӣз”ҹеӯЈпјҢе…ідәҺжӢӣз”ҹеҗҚйўқзҡ„еҲҶй…Қй—®йўҳпјҢе…ідәҺеҗҚж ЎжҠўз”ҹжәҗеј•еҸ‘зҡ„еҗ„зұ»жҳҺдәүжҡ—ж–—еҸҲеҶҚдёҖж¬Ўе‘ҲзҺ°еңЁиҒҡе…үзҒҜдёӢпјҢеңЁж•ҷиӮІе…¬е№іиҜүжұӮи¶ҠжқҘи¶ҠејәзғҲзҡ„еҪ“дёӢпјҢжӮЁеҝғдёӯзҡ„ж•ҷиӮІд№ҢжүҳйӮҰжҳҜдёӘжҖҺд№Ҳж ·зҡ„жҷҜиұЎпјҹ
дҪ•жҖҖе®Ҹпјҡж•ҷиӮІиө„жәҗзҡ„еҲҶй…ҚпјҢеә”иҜҘйҒөеҫӘе…¬е№ізҡ„еҺҹеҲҷпјҢзҺ°жңүзҡ„ж•ҷиӮІиө„жәҗпјҢдёәдәҶиҝӣиЎҢжӣҙе…¬е№ізҡ„еҲҶй…ҚпјҢеҸҜд»ҘиҖғиҷ‘еҜ№дәҺејұеҠҝең°еҢәе’ҢејұеҠҝзҫӨдҪ“иҝӣиЎҢиө„йҮ‘е’ҢеҗҚйўқдёҠзҡ„ж”ҜжҢҒпјҢдҪҶжҳҜиҝҳжңүдёҖдёӘй—®йўҳжҳҜејҖжәҗ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еә”иҜҘжіЁйҮҚж•ҷиӮІиө„жәҗзҡ„ејҖж”ҫе’ҢжҸҗеҚҮпјҢеҢ…жӢ¬ејҖж”ҫж°‘й—ҙзҡ„гҖҒеӣҪеӨ–зҡ„иө„жәҗпјҢеә”иҜҘжҳҜеӨҡжәҗејҖжөҒгҖӮ
ж•ҷиӮІж”№йқ©зҡ„дәүи®®еЈ°дёҚж–ӯпјҢдҪҶеҰӮжһңжҠҠй«ҳиҖғиҝҷдёҖиҖғиҜ•еҲ¶еәҰж”№жҺүпјҢжӣҙе®№жҳ“йҖ жҲҗдёҚе…¬е№іпјҢжӣҙе®№жҳ“иў«зү№жқғеҲ©з”ЁгҖӮ
дёҚе®ўж°”ең°иҜҙпјҢиҝ‘дәӣе№ҙдёӯеӣҪзҡ„дёҖдәӣж•ҷиӮІж”№йқ©пјҢдёҚжҳҜж”№еҫ—жӣҙеҘҪдәҶпјҢиҖҢжҳҜж”№еҫ—жӣҙе·®дәҶгҖӮдёҠдё–зәӘ80-90е№ҙд»Јзҡ„еӯ©еӯҗпјҢиҜ»е°ҸеӯҰгҖҒдёӯеӯҰпјҢ并没жңүеҫҲжІүйҮҚзҡ„еӯҰдёҡиҙҹжӢ…пјҢжІЎжңүе°ҸеҚҮеҲқгҖҒдёӯиҖғзӯүеҗ„з§ҚвҖңеҚ еқ‘зҸӯвҖқпјҢдҪҶзҺ°еңЁзҡ„еӯ©еӯҗпјҢеҰӮжһңдёҚеҸӮеҠ еҗ„зұ»д»ҘвҖңеҚ еқ‘вҖқдёәеҗҚд№үзҡ„иҫ…еҜјзҸӯпјҢдёҚиҜ·е®¶ж•ҷпјҢе°ұжІЎжңүеҠһжі•еңЁзҺ°жңүзҡ„ж•ҷиӮІдҪ“еҲ¶дёӯеҚ жңүдјҳеҠҝгҖӮ
ж•ҷиӮІж”№йқ©жҺЁиҝӣдәҶдёҖдәҢеҚҒе№ҙпјҢж №жң¬жҖ§зҡ„дёңиҘҝжІЎжңүж”№еҸҳпјҢж”№йқ©еә”иҜҘејҖжәҗпјҢеҚіи®©ж•ҷиӮІиө„жәҗеӨҡиҪЁеҲ¶пјҢйҖҡиҝҮеӨҡиҪЁеҲ¶еҲҶжөҒпјҢи®©жҜҸдёӘжөҒеҗ‘йғҪиғҪеҒҡеҲ°жқ°еҮәпјҢиҖҢдёҚд»…жҳҜи®©жүҖжңүзҡ„еӯҰз”ҹзӣҜзқҖеҮ жүҖз»јеҗҲжҖ§зҡ„еҗҚзүҢеӨ§еӯҰгҖӮд»ҘзҫҺеӣҪдёәдҫӢпјҢж—ўжңүеҫҲеҘҪзҡ„з»јеҗҲжҖ§з§Ғз«ӢеӨ§еӯҰе’Ңе…¬з«ӢеӨ§еӯҰпјҢд№ҹжңүи®ёеӨҡзІҫиҮҙзҡ„е°ҸеһӢж–ҮзҗҶеӯҰйҷўпјҢе…¶ж•ҷеӯҰиҙЁйҮҸдёҚдәҡдәҺйӮЈдәӣжңҖи‘—еҗҚзҡ„еӨ§еӯҰгҖӮиҝҳжңүеғҸеҫ·еӣҪзӯүжңүи®ёеӨҡжҠҖжңҜеӯҰйҷўе’ҢеӯҰж ЎпјҢеӯҰз”ҹеҮәжқҘзҡ„е·ҘдҪңе’Ң收е…ҘеүҚжҷҜйғҪзӣёеҪ“д№ӢеҘҪгҖӮ
жҫҺж№ғж–°й—»пјҡжңүдёҖз§ҚиҜҙжі•пјҢдёӯеӣҪеҫҲеӨҡеӯҰз”ҹеҜ№дәҺж•ҷиӮІж”№йқ©зҡ„жҲҗж•ҲеңЁвҖңз”Ёи„ҡжҠ•зҘЁвҖқпјҢзә·зә·иө°еҮәеӣҪй—ЁиҜ»д№ҰгҖӮдјҳз§Җз”ҹжәҗзҡ„жөҒеӨұпјҢдјҡдёҚдјҡи®©дёӯеӣҪеӨ§еӯҰиҝҪжұӮдё–з•ҢдёҖжөҒд№Ӣи·Ҝ延й•ҝпјҹ
дҪ•жҖҖе®ҸпјҡдёӯеӣҪзҡ„ж•ҷиӮІеӨӘиҝҮз»ҹдёҖпјҢеҚғж ЎдёҖйқўпјҢеӨ§иҖҢе…ЁпјҢдёҚжҳҜеӨӘеҰҘеҪ“пјҢеҫҲеӨҡеӨ§еӯҰйғҪе–ҠеҮәдәҶиө¶и¶…зҡ„еҸЈеҸ·пјҢиҰҒвҖңдәүеҲӣдё–з•ҢдёҖжөҒеӨ§еӯҰвҖқпјҢдҪҶжҲ‘们зҺ°еңЁзҰ»дё–з•ҢдёҖжөҒеӨ§еӯҰжҳҜи¶ҠжқҘи¶Ҡиҝ‘пјҢиҝҳжҳҜи¶ҠжқҘи¶ҠиҝңдәҶпјҹ
дёҖжөҒеӨ§еӯҰиҰҒжңүеҘҪзҡ„з”ҹжәҗпјҢжңҖеҘҪзҡ„еӨ§еӯҰеҗёеј•жңҖеҘҪзҡ„еӯҰз”ҹпјҢдҪҶ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зҡ„дёӯеӣҪдјҳз§ҖеӯҰз”ҹйҖүжӢ©дәҶеҮәеӣҪз•ҷеӯҰпјҢеҢ—дә¬дёҠжө·е№ҝе·һдёҖзәҝеҹҺеёӮзҡ„дёҖдәӣжңҖдјҳз§Җзҡ„еӯҰз”ҹпјҢ他们зҡ„зңјйҮҢзҡ„зӣ®ж Үе·Із»ҸдёҚеҸӘжҳҜжё…еҚҺеҢ—еӨ§гҖӮиҖҢдё”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зҡ„еӯҰз”ҹдёҚеҸӘжҳҜжң¬з§‘йҳ¶ж®өпјҢз”ҡиҮіеңЁдёӯеӯҰйҳ¶ж®өе°ұйҖүжӢ©дәҶеҮәеӣҪгҖӮ他们дёәд»Җд№ҲзҰ»ејҖдәҶпјҹеҰӮжһңжҲ‘们зҡ„ж•ҷиӮІдёҚиғҪеҗёеј•дёҖжөҒзҡ„еӯҰз”ҹпјҢиҝҳжҖҺд№ҲеҲӣдёҖжөҒеӨ§еӯҰпјҹ
еҜ№дәҺж•ҷиӮІиҖҢиЁҖпјҢйҮҚиҰҒзҡ„жҳҜдёӨз«ҜпјҢеҗёеј•жңҖдјҳз§Җзҡ„е’Ңж”ҜжҢҒеӨ„еўғжңҖејұзҡ„пјҢдёӨз«ҜйғҪдёҚиғҪеҝҪз•ҘгҖӮ
жҫҺж№ғж–°й—»пјҡд»ҘеүҚвҖңеЈ«еӨ§еӨ«еӨҡеҮәиҚүйҮҺвҖқпјҢеҚідҪҝдёүд»ЈеҠЎеҶңзҡ„еҶңжқ‘еӯҗејҹпјҢд№ҹиғҪйҖҡиҝҮ科дёҫеҲ¶еәҰиҝӣе…Ҙжңқе ӮпјҢжӮЁжҖҺд№ҲзңӢпјҹ
дҪ•жҖҖе®ҸпјҡдёӯеӣҪеҺҶеҸІдёҚеҗҢдәҺиҘҝж–№зҡ„и·Ҝеҫ„пјҢдёӯеӣҪзҡ„科дёҫеҲ¶еәҰжңүе…¶дјҳи¶ҠжҖ§пјҢи§ЈеҶідәҶз»ҹжІ»иҖ…е’Ңиҙөж—ҸеңЁйқўеҜ№иҮӘе·ұзҡ„еӯҗеҘіе®үзҪ®й—®йўҳж—¶пјҢеҰӮдҪ•еңЁеҲ¶еәҰзҡ„зәҰжқҹдёӢеҸ–еҫ—е№іиЎЎгҖӮ
иҝҮеҺ»иҘҝж–№ж–ҮжҳҺжІЎжңүжүҫеҲ°йҖӮеҗҲзҡ„и·Ҝеҫ„пјҢеҺҶеҸІдёҠжІЎжңүе“ӘдёҖз§Қж–ҮжҳҺеғҸдёӯеӣҪиҝҷд№ҲжҲҗеҠҹең°йҖҡиҝҮиҖғиҜ•еҲ¶еәҰжҠҠжқғй’ұеҗҚиҝӣиЎҢ规иҢғпјҡж”ҝжІ»зҡ„зЎ®жҳҜжңҖеӨ§зҡ„иө„жәҗпјҢе®ҳжң¬дҪҚеңЁдёӯеӣҪй•ҝжңҹеӯҳеңЁпјҢдҪҶеҪ“е®ҳеҝ…йЎ»йҖҡиҝҮиҖғиҜ•пјҢзҺӢе…¬иҙөж—Ҹзҡ„еӯҗеҘідёҖиҲ¬д№ҹеҝ…йЎ»йҖҡиҝҮиҖғиҜ•жүҚиғҪеҒҡе®ҳпјҢиҖ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еҚідҪҝеҶңжқ‘иҙ«еҜ’зҡ„еӯ©еӯҗйҖҡиҝҮ科дёҫеҲ¶еәҰпјҢд№ҹжңүжҲҗеҠҹзҡ„жңәдјҡпјҢжүҖд»ҘйӮЈж—¶еҖҷвҖңеЈ«еӨ§еӨ«еӨҡеҮәиҚүйҮҺвҖқпјҢиҰҒиҝӣе…ҘдёҠжөҒзӨҫдјҡе’Ңз»ҹжІ»йҳ¶еұӮпјҢеҝ…йЎ»иҰҒдјҡиҜ»д№ҰпјҢ科дёҫиҖғиҜ•зҡ„е…«иӮЎж–Үе…¶е®һжҳҜиғҪиҖғеҮәиғҪеҠӣзҡ„пјҢйңҖиҰҒиҖғз”ҹжңүзҗҶи§ЈеҠӣгҖҒи®°еҝҶеҠӣе’Ңж–ҮеӯҰзҡ„иЎЁиҫҫиғҪеҠӣгҖӮ
еҸӨеҫҖд»ҠжқҘпјҢдәәж–ҮжҳҜжңҖйҡҫе®ўи§ӮеҢ–гҖҒж ҮеҮҶеҢ–зҡ„пјҢдҪҶдёӯеӣҪдәәеҚҙеҫҲиҒӘжҳҺең°жҠҠдәәж–Үзҡ„иҖғжҹҘеҸҳжҲҗдәҶе®ўи§ӮеҢ–гҖҒж ҮеҮҶеҢ–зҡ„иҖғиҜ•пјҢиҝҷдёҺдёӯеӣҪзҡ„иҜӯиЁҖжңүе…іпјҢдёӯж–Үжұүеӯ—жңүе…¶зӢ¬зү№зҡ„йӯ…еҠӣпјҢиҝҷд№ҹеҸӘжңүдёӯеӣҪжүҚиғҪеҒҡеҲ°пјҢе…¶д»–ж–ҮжҳҺжІЎжңүеҒҡеҲ°гҖӮдҪҶдёӯеӣҪзҡ„科дёҫеҲ¶еәҰ并没жңүеңЁдё–з•ҢеҸІгҖҒж”ҝжІ»еҸІдёҠеј•иө·и¶іеӨҹзҡ„йҮҚи§ҶпјҢ科дёҫеҲ¶еәҰдёҚд»…д»…жҳҜж•ҷиӮІеҲ¶еәҰпјҢжҳҜж”ҝжІ»еҲ¶еәҰпјҢиҝҳеЎ‘йҖ дәҶзӨҫдјҡз»“жһ„гҖӮйҡҸзқҖ1905е№ҙеәҹйҷӨ科дёҫпјҢдёӯеӣҪзҡ„зӨҫдјҡз»“жһ„еҸ‘з”ҹдәҶжһҒеӨ§зҡ„ж”№еҸҳгҖӮ
дҪҶжҳҜзҺ°д»ЈдёӯеӣҪеҫҲйҡҫеҜ№д»ҘеҫҖзҡ„иҝҷдёҖеҲ¶еәҰиҝӣиЎҢзӣҙжҺҘеҖҹйүҙе’Ңжҗ¬з”ЁпјҢйӮЈж—¶еҖҷеӣҪ家еҠҹиғҪе°‘пјҢеҮ дәҝдәәж°‘еҸӘйңҖиҰҒеҮ дёҮж–Үе®ҳиҝӣиЎҢз®ЎзҗҶпјҢзҺ°д»ЈзӨҫдјҡдё»иҰҒжҳҜз»ҸжөҺеҸ–еҗ‘пјҢеӣҪ家еҠҹиғҪеҸ‘з”ҹдәҶж”№еҸҳпјҢе®ҳе‘ҳе’ҢиӯҰеҜҹзҡ„дәәж•°дёҺеҪ“е№ҙд№ҹдёҚеҸҜеҗҢж—ҘиҖҢиҜӯгҖӮдёӯеӣҪзҡ„дј з»ҹзӨҫдјҡжҳҜй«ҳеәҰиҮӘжІ»зҡ„пјҢеҫҲеӨҡдәәжҲ·еҸЈйғҪжІЎжңүпјҢд№ҹдёҚйңҖиҰҒеӨ§йҮҸжҠҘзЁҺпјҢжңүеҫҲеӨҡж–№йқўжҳҜе…ҚзЁҺзҡ„пјҢиҮӘз”ұеәҰд№ҹй«ҳпјҢз»ҸжөҺжҙ»еҠЁд№ҹиҮӘз”ұгҖӮ
и°ҲеёҲеҫ·пјҡвҖңеҜјеёҲжҲҗиҖҒжқҝвҖқжҳҜж•ҷиӮІејӮеҢ–пјҢиҰҒдҝқжҠӨдёҖеҝғз ”з©¶й«ҳзә§еӯҰй—®зҡ„иҖҒеёҲ
жҫҺж№ғж–°й—»пјҡд»Ҡе№ҙ4жңҲжӮЁеңЁеҢ—дә¬еӨ§еӯҰеӯҰе·ҘйғЁз»„з»Үзҡ„ж•ҷжҺҲиҢ¶еә§дёҠе’ҢеӯҰз”ҹ们дәӨжөҒжҺўи®ЁпјҢи°ҲеҲ°вҖңеӨ§еӯҰзҡ„жң¬иҙЁжҳҜдёҖдёӘеәҮжҠӨжүҖвҖқпјҢи°ҲеҲ°вҖңзңҹжӯЈзҡ„еӨ§еӯҰиҖҒеёҲеә”иҜҘе…·еӨҮиғҪеӨҹиў«ж„ҹеҠЁе№¶дё”иғҪеӨҹж„ҹеҠЁеҲ«дәәиҝҷдёӨдёӘзү№зӮ№вҖқпјҢдҪҶзҺ°еңЁи¶ҠжқҘи¶ҠжҖҘеҠҹиҝ‘еҲ©зҡ„зӨҫдјҡйЈҺж°”дҫөиўӯж ЎеӣӯпјҢйғЁеҲҶеӯҰз”ҹеҸ—дёҚжӯЈд№ӢйЈҺеҪұе“ҚпјҢе’ҢиҖҒеёҲд№Ӣй—ҙзҡ„关系并дёҚеҰӮеҮ еҚҒе№ҙеүҚзәҜзІ№пјҢиҝҳжңүдёҖдәӣиҖҒеёҲеҲ©з”ЁеӯҰз”ҹпјҢеҜ№еӯҰз”ҹеҒҡеҮәдёҚз¬ҰеҗҲиЎҢдёә规иҢғзҡ„дёҚйҒ“еҫ·дәӢ件пјҢжҜ”еҰӮеүҚдёҚд№…еҚҺдёңзҗҶе·ҘеӨ§еӯҰзҡ„з ”з©¶з”ҹжӯ»дәҺеҜјеёҲзҡ„е·ҘеҺӮдәӢ件пјҢйқўеҜ№иҝҷж ·зҡ„ж Ўеӣӯз§Қз§ҚжҖӘзҺ°иұЎпјҢжӮЁдёӘдәәзҡ„и§ӮзӮ№жҳҜд»Җд№Ҳпјҹ
дҪ•жҖҖе®ҸпјҡеӨ§еӯҰйҮҢдё»иҰҒжңүдёӨйғЁеҲҶдәәпјҢиҖҒеёҲе’ҢеӯҰз”ҹпјҢжңҖйҮҚиҰҒжҳҜе…ізі»е°ұжҳҜеёҲз”ҹе…ізі»пјҢдёӯеӣҪзҡ„еӨ§еӯҰдёҖжҳҜеҸ—жқғеҠӣе№Ійў„пјҢдёҖжҳҜеҸ—еёӮеңәеҪұе“ҚпјҢжІЎжңүиЎҢж”ҝз®ЎзҗҶе’ҢдёҚиҖғиҷ‘еёӮеңәйңҖжұӮиҮӘ然д№ҹдёҚиЎҢпјҢдҪҶжңүдәӣеӯҰ科зҡ„иҖҒеёҲжҠҠеӯҰз”ҹеҪ“жҲҗжү“е·Ҙд»”иҮӘ然жҳҜж•ҷиӮІејӮеҢ–пјҢд»ҺиҖҢеҜјиҮҙдәҶеҫҲеӨҡй—®йўҳзҡ„еҮәзҺ°гҖӮ
еӨ§еӯҰйңҖиҰҒејәи°ғеӯҰз”ҹжң¬дҪҚпјҢдҪҶиҖҒеёҲд№ҹеҫҲйҮҚиҰҒпјҢиҖҒеёҲжҺҢжҸЎжҹҗз§ҚиҜқиҜӯжқғпјҢз”ҡиҮідё»еҜјжқғпјҢиҖҒеёҲзҡ„йҮҚиҰҒжҖ§дё»иҰҒдҪ“зҺ°еңЁдёӨдёӘж–№йқўпјҢдёҖжҳҜзҹҘиҜҶпјҢдәҢжҳҜеҒҡдәәгҖӮзҹҘиҜҶд»…жҳҜжүӢж®өе’Ңе·Ҙе…·иҖҢдёҚжҳҜзӣ®зҡ„пјҢиҖҒеёҲеә”иҜҘеҜ№зҹҘиҜҶжң¬иә«жңүејәзғҲзҡ„е…ҙи¶ЈпјҢдёҚйңҖиҰҒеӨ–з•Ңзҡ„иҖғиҜ„д№ҹжҳҜз»Ҳе…¶дёҖз”ҹжғіеҒҡзҡ„дәӢжғ…пјҢзңӢеҲ°зҹҘиҜҶиғҢеҗҺзҡ„зңҹе–„зҫҺпјҢиў«еҗҺйқўзҡ„дёңиҘҝж„ҹеҠЁпјҢж„ҹеҠЁиҮӘе·ұд№ҹж„ҹеҠЁеҲ«дәә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ж„ҹеҠЁеҗҢеӯҰпјҢиҝҳжңүдәӣиҖҒеёҲиғҪеӨҹеҮӯеҖҹиҮӘе·ұеҜ№зҹҘиҜҶзҡ„е…ҙи¶ЈпјҢеҶҚиҝӣиЎҢе…·жңүеҲӣйҖ жҖ§зҡ„ејҖеҸ‘гҖӮиҝҷж ·зҡ„иҖҒеёҲзҡ„еӯҳеңЁпјҢеҜ№дәҺдёҖжүҖеӨ§еӯҰе°Өе…¶йҮҚиҰҒпјҢдёҖжүҖеӨ§еӯҰзҡ„ж Ўй•ҝпјҢжңҖйҮҚиҰҒзҡ„дәӢе°ұжҳҜжүҫеҲ°е°ҪйҮҸеӨҡеҘҪзҡ„иҖҒеёҲгҖӮ
дёҫдёӘдёҚдёҖе®ҡеҫҲиҙҙеҲҮзҡ„дҫӢеӯҗпјҢиҘҝеҚ—иҒ”еӨ§ж—¶жңҹжқЎд»¶еҫҲе·®дҪҶеӨ§еёҲдә‘йӣҶгҖҒдәәжүҚиҫҲеҮәпјҢзҺ°еңЁзҡ„еӨ§еӯҰпјҢеӨ§жҘјеӨҡдәҶпјҢеӨ§еёҲе°‘дәҶпјҢеҚідҪҝжңүеӨ§еёҲжүҚиғҪзҡ„дәәпјҢд№ҹе®№жҳ“иў«ж·№жІЎпјҢиў«еҶІеҮ»пјҢиҮӘе·ұдёҚзӣёдҝЎиҮӘе·ұпјҢи®ӨдёәиҮӘе·ұиҝҷж ·зҡ„еҒҡжі•жҳҜдёҚжҳҜеӨӘејӮзұ»гҖӮеӨ§еӯҰйҮҢжҳҜеӯҳеңЁиҝҷж ·дёҖйғЁеҲҶдәәзҡ„пјҢж Ўй•ҝе’Ңз®ЎзҗҶеұӮзҡ„дҪңз”Ёе°ұжҳҜ让他们дёҚиғҪеӨӘиҫ№зјҳпјҢжңүдәҶдёҖжөҒзҡ„иҖҒеёҲжүҚиғҪеҗёеј•жңҖдјҳз§Җзҡ„еӯҰз”ҹпјҢ他们зҡ„е…ҙи¶ЈжүҖеңЁжҳҜз ”з©¶й«ҳзә§еӯҰй—®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еҒҡй«ҳе®ҳпјҢдёҚиҰҒ让他们被淹没гҖҒиў«иҫ№зјҳеҢ–дәҶпјҢ жңҖеҘҪзҡ„еӯҰз”ҹд»ҺеҘҪзҡ„иҖҒеёҲйӮЈйҮҢиҺ·еҫ—зҒөйӯӮжҖ§зҡ„дёңиҘҝпјҢе°ҶдёҖз”ҹеҸ—з”ЁгҖӮ他们еҜ№дәҺзңҹзҗҶгҖҒжҷәж…§пјҢжңүеҫҲж·ұзҡ„ж„ҹеҠЁпјҢдёҖз”ҹдёўдёҚжҺүпјҢеӨ§еӯҰж—¶е…үд№ҹжҲҗдёәдәҶ他们жңҖе®үж…°пјҢжңҖе№ёзҰҸзҡ„ең°ж–№гҖӮ
жҫҺж№ғж–°й—»пјҡзӨҫдјҡеёёеёёеңЁж„ҹеҸ№пјҢиҝҪеҝҶж°‘еӣҪж—¶д»Јзҡ„еӯҰжңҜж°ҙе№іпјҢжӮЁи§үеҫ—зҺ°еңЁзҡ„ж•ҷиӮІж°ҙе№іжҳҜдёӢйҷҚдәҶд№Ҳпјҹ
дҪ•жҖҖе®ҸпјҡзҺ°еңЁзҡ„ж•ҷеёҲж°ҙе№іж•ҙдҪ“дёҠд№ҹ许并дёҚдҪҺдәҺж°‘еӣҪж—¶д»Јзҡ„ж°ҙе№ігҖӮжҲ‘еҜ№дәҺзҺ°еңЁзҡ„е№ҙиҪ»ж•ҷеёҲжҳҜзңӢеҘҪзҡ„пјҢ他们жҳҜеҸ—иҝҮеҫҲеҘҪи®ӯз»ғзҡ„дёҖд»ЈдәәпјҢжҜ”еҰӮ他们зҡ„еӨ–иҜӯи®ӯз»ғжӣҙзІҫиҮҙгҖҒжӣҙз»ҶеҢ–пјҢжҳҜе……ж»ЎеёҢжңӣзҡ„дёҖд»ЈдәәгҖӮ
зҺ°еңЁеҫҲеӨҡдәәйғҪжҠҠзҺ°д»Је’Ңж°‘еӣҪжңҹй—ҙзҡ„еӯҰжңҜиҝӣиЎҢжҜ”иҫғпјҢж°‘еӣҪеҪ“然жңүе…¶дјҳи¶ҠжҖ§пјҢдҪҶеҪ“д»ҠдёӯеӣҪз»ҸиҝҮеҮ еҚҒе№ҙзҡ„ж”№йқ©ејҖж”ҫпјҢеҗ„з§Қеҗ„ж ·зҡ„иө„жәҗи¶ҠжқҘи¶Ҡдё°еҜҢпјҢ зҺ°еңЁзҡ„еӯҰжңҜзҹҘиҜҶзі»з»ҹжӣҙе®Ңе–„пјҢеӯҰ科жӣҙйҪҗе…ЁдәҶпјҢ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йҳҹдјҚзҡ„дё“дёҡеҢ–зЁӢеәҰе’ҢзҹҘиҜҶзі»з»ҹзҡ„ж”№е–„жҳҜжӣҙејәзҡ„гҖӮиҷҪ然жңҖй«ҳзӮ№е’Ңж°‘еӣҪж—¶жңҹзҡ„еӨ§еёҲжҜ”иҫғиҝҳжңүе·®и·қпјҢдҪҶжҳҜеңЁйҮҚзӮ№еӨ§еӯҰйҮҢзҡ„ж•ҙдҪ“зҙ иҙЁиҝҳжҳҜзӣёеҪ“дёҚй”ҷпјҢеңЁйҖӮеҪ“зҡ„ж—¶еҖҷжҲ–и®ёдјҡи„ұйў–иҖҢеҮәдёҖдәӣеӨ§еёҲжҲ–еҮҶеӨ§еёҲгҖӮ
и°Ҳз”ҹе‘Ҫж•ҷиӮІпјҡиҮӘжқҖйў‘зҺ°жҳҜеӣ дёәжӣҙйҮҚжҷәеҠӣж•ҷиӮІпјҢжІЎеҹ№е…»еӯ©еӯҗеҜ№з”ҹе‘Ҫзҡ„зғӯзҲұ
жҫҺж№ғж–°й—»пјҡжӮЁзҡ„гҖҠзҸҚйҮҚз”ҹе‘ҪгҖӢдёҖд№Ұ1996е№ҙз”ұе№ҝдёңж•ҷиӮІеҮәзүҲзӨҫеҮәзүҲпјҢйҰҷжёҜдёүиҒ”д№Ұеә—е’ҢеҸ°ж№ҫд№Ұжһ—еҮәзүҲжңүйҷҗе…¬еҸёд№ҹеҗҢжӯҘеҮәзүҲпјҢгҖҠзҸҚйҮҚз”ҹе‘ҪгҖӢиҝҳиҺ·дәҶ1998е№ҙе…ЁеӣҪйқ’е°‘е№ҙиҜ»зү©дёҖзӯүеҘ–пјҢзҺ°еңЁзҡ„йқ’е°‘е№ҙиў«з§°дёәвҖңеұҸдёҖд»ЈвҖқпјҢ他们еңЁз”өеӯҗдә§е“Ғзҡ„еҢ…еӣҙдёӯжҲҗй•ҝпјҢеҜ№дәҺиҷҡе№»зҡ„дё–з•ҢеҫҲжІүиҝ·пјҢиҪ»з”ҹгҖҒжҠ‘йғҒзӯүжғ…еҶөеңЁзҺ°еңЁзҡ„еӨ§еӯҰз”ҹз”ҡиҮідёӯе°ҸеӯҰз”ҹзҫӨдҪ“дёӯйў‘еҸ‘пјҢжӮЁи§үеҫ—иҰҒи§ЈеҶіиҝҷж ·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жңүд»Җд№ҲвҖңи§ЈиҚҜвҖқд№Ҳпјҹ
дҪ•жҖҖе®ҸпјҡеҜ№дәҺзҺ°еңЁзҡ„вҖңеұҸдёҖд»ЈвҖқзҡ„е№ҙиҪ»дәәпјҢдёҚиҰҒиҝҮеҲҶжү№иҜ„гҖӮеҚідҪҝжҳҜжҲ‘们иҝҷж ·еӣӣдә”еҚҒеІҒзҡ„жҲҗе№ҙдәәпјҢзҹҘиҜҶжқҘжәҗд№ҹеңЁ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ең°йҖҡиҝҮжүӢжңәжҲ–иҖ…з”өеӯҗеұҸ幕гҖӮдҝЎжҒҜзҡ„еӨҡе…ғеҢ–з”ҡиҮізҪ‘з»ңеҢ–д№ҹе·Із»ҸжҲҗдёәдәҶдё»жөҒпјҢж—¶д»ЈеңЁеҸ‘еұ•пјҢзӨҫдјҡзҡ„еҸҳеҢ–еӨӘеӨ§пјҢеҪ“е№ҙзҡ„дёҖдәӣз»ҸйӘҢж”ҫеҲ°зҺ°еңЁдёҚдёҖе®ҡйҖӮз”ЁгҖӮ
жҜ”еҰӮд»ҘеҫҖжүҖиҜҙзҡ„еҜ№еӯ©еӯҗзҡ„йҳ…иҜ»д»Ҙз»Ҹе…ёдёәдё»пјҢдҪҶдёҚжҳҜйҖӮз”ЁжүҖжңүзҡ„еӯ©еӯҗпјҢеҜ№дәәж–Үж„ҹе…ҙи¶Јзҡ„еӯ©еӯҗпјҢеҸҜд»Ҙдё»еј д»–д»¬еӨҡиҜ»иҜ»еҸӨзұҚгҖӮдҪҶ并йқһжүҖжңүеӯ©еӯҗйғҪиҰҒеҺ»иҜ»еҸӨзұҚпјҢж—¶д»Је°ұжҳҜиҝҷж ·зҡ„пјҢеҰӮжһңе…¶д»–еӯ©еӯҗйғҪеҜ№з”өеӯҗдә§е“ҒдәҶеҰӮжҢҮжҺҢпјҢдёҚдәҶи§Јзҡ„еӯ©еӯҗе°ұе®№жҳ“еңЁж—¶д»ЈдёӯиҗҪдјҚпјҢе°ұж— жі•е’ҢеҗҢйҫ„дәәйЎәз•…ең°дәӨжөҒпјҢеӣ дёәе…ұеҗҢиҜӯиЁҖеӨӘе°‘гҖӮ
еҜ№дәҺйқ’е°‘е№ҙиҖҢиЁҖпјҢйңҖиҰҒз”өеӯҗдә§е“ҒпјҢдҪҶдёҚиҰҒеӨӘжІүиҝ·з”өеӯҗдә§е“ҒпјҢж— и®әжҳҜвҖңеұҸдёҖд»ЈвҖқиҝҳжҳҜвҖңе®…е°‘е№ҙвҖқпјҢдҪңдёәж•ҷеёҲ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家й•ҝпјҢйңҖиҰҒеј•еҜјзҡ„жҳҜдёҚиғҪ让他们еӨӘжІүиҝ·пјҢиҰҒе°ҪйҮҸжҠҠ他们вҖңиө¶еҮәеҺ»вҖқпјҢ让他们еӨҡеҺ»жҲ·еӨ–пјҢз”ЁдҪ“иӮІе’ҢжёёжҲҸзӯүжҲ·еӨ–иҝҗеҠЁпјҢеҶІж·ЎеұҸ幕зҡ„иҝҮеӨҡеҗёеј•еҠӣгҖӮзғӯиЎ·жҲ·еӨ–иҝҗеҠЁпјҢеӨҡж„ҹи§үдёҖдёӢиҮӘ然з•Ңзҡ„вҖңз”ҹз”ҹдёҚжҒҜвҖқпјҢд№ҹжҳҜеңЁеҹ№е…»еҜ№з”ҹе‘Ҫзҡ„зғӯзҲұгҖӮжҲ‘жңүж—¶зңӢеҲ°дёҖдәӣеӯ©еӯҗеҲ°дәҶдёҖдәӣеЈ®йҳ”зҡ„иҮӘ然зҫҺжҷҜд№ӢеүҚпјҢиҝҳжҳҜеңЁдҪҺеӨҙзңӢжүӢжңәе’Ңе№іжқҝпјҢзңҹжҳҜж„ҹеҲ°еҸҜжғңгҖӮ
еҰӮжһңеӯ©еӯҗиҮӘе·ұеҜ№иҮӘе·ұжңүдёҖз§ҚејәзғҲзҡ„иҮӘдҝЎпјҢеҜ№з”ҹе‘ҪжңүзғӯзҲұпјҢе°ұдјҡжӣҙеҠ зҸҚжғңз”ҹе‘ҪпјҢйў‘йў‘еҮәзҺ°зҡ„иҮӘжқҖдәӢ件д»Өдәәеҝ§еҝғпјҢеҸҜиғҪжңүдёҖдёӘеҺҹеӣ жҳҜдёҖдәӣж•ҷеёҲе’Ң家й•ҝеӨӘжіЁйҮҚжҷәеҠӣж•ҷиӮІпјҢиҖҢжІЎжңүи®©еӯ©еӯҗиҲ’еұ•еҝ«д№җпјҢз”ҹе‘Ҫж•ҷиӮІзҡ„зңҹи°ӣжҳҜи®©еӯ©еӯҗжҲҗдёәжңүз”ҹж°”зҡ„дәә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жһҜжңЁпјҢй•ҝжңҹж”ҫеңЁеұӢеӯҗйҮҢпјҢжҳҜдёҚеҸҜиғҪеҸ‘иҠҪзҡ„пјҢз”ҡиҮіжҳҜз—…жҖҒзҡ„пјҢеә”иҜҘжҠҠеӯ©еӯҗиө¶еҮәеҺ»пјҢ让他们еӨҡеӨҡеҸӮеҠ жҲ·еӨ–жҙ»еҠЁпјҢејәеҒҘиә«еҝғгҖӮ
жң¬ж–Үз»“жқҹпјҢеӨҡи°ўйҳ…иҜ»пјҒ | 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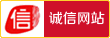 Powered by Discuz! X3.4 © 2008-2024 жё еҺҝзҪ‘ зүҲжқғжүҖжңү иңҖICPеӨҮ2021001069еҸ·-4 е·қе…¬зҪ‘е®үеӨҮ51172502000170еҸ·
жҠҖжңҜж”ҜжҢҒ: е…Ӣзұіи®ҫи®Ў
Powered by Discuz! X3.4 © 2008-2024 жё еҺҝзҪ‘ зүҲжқғжүҖжңү иңҖICPеӨҮ2021001069еҸ·-4 е·қе…¬зҪ‘е®үеӨҮ51172502000170еҸ·
жҠҖжңҜж”ҜжҢҒ: е…Ӣзұіи®ҫи®Ў